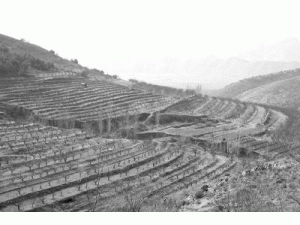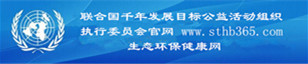东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表示,鉴定许可证有效期限为5年,到期后司法鉴定管理处很有可能不再给延长期限,虽然没有吊销许可证,但实际上来讲该司法鉴定中心已因此事名存实亡。
案归原点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河南东村看到,许多2007年以后死掉的果树至今仍立在山间。村民们说,这些死树所处的位置本来可以重新栽种,但由于事情迟迟没能解决,为保留证据,他们只能继续遭受损失。
“无论如何,必须要个结果。”许多果农表示,8年诉讼生涯已让他们没有后路,只能咬牙坚持下去。
“我太痛恨污染了,这让我40岁的时候失了业,只能出去打工。”原本在当地纺织厂上班的果农喻建东说,为了专心经营果园,他于1994年辞掉了工作,现在果树死了,创业梦化为泡影。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诉讼部部长刘湘认为,事已至此,由于其中牵涉法院失职和赔偿金额巨大等问题,恐怕司法部门一时难以抉择。
“如果能翻案或调解,我们将向企业索赔3000多万元的损失。”杜业龙说,多年的损失累计相加,数额已相当巨大,事情拖得越久,越不利于解决。
金峰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刚表示,企业绝不会同意调解,因为公司始终坚信,果树死亡的原因与污染无关。此外,环保案件适用于举证倒置原则,倘若时隔8年后案件发回重审,企业肯定无法接受。
“东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如果真要撤销他们当时的司法鉴定,我们企业有可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连同鉴定中心一起诉讼。”他说。
金峰铜业有限公司原来的负责人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果农们走上这条常年告状之路与地方政府当初的不当作为有着直接关系。
这位负责人表示,污染发生后,政府逼迫企业多拿出200多万元赔偿百姓,后又以“更新改造”为名,每年为这3000亩受污果园补贴450万元资金,助长了受害果农的“胃口”,才造成了今天告状不断的局面。
“政府相当于拿钱‘赞助’百姓去告状,搞得树也死了,地也荒了。”他说。
喀喇沁旗政府部门的一些干部坦言,“更新改造”项目确实只针对河南东村的受污染果园,目的是安抚果农“原本打算补贴三年时间,但由于百姓不干,该项目至今未停。”一位干部说。
一些种植农作物的村民表示,他们在金峰铜业周边种植的作物近年来长势很差,为了补偿损失,政府还曾出面以“灾救款”的形式发放过补贴,但并不允许被补贴农民向外提及污染的事情。
喀喇沁旗环保局副局长李军表示,涉事企业和为其配套的氟化工企业为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近年来未出现超标排放。但记者手中一份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心2013年7月23日作出的调查报告显示,两个企业周边部分时段环境空气中的氟化物浓度明显大于城市地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浓度限值,浓度最高时甚至达到国家规定的21倍。
行政“和稀泥”
刘湘认为,恰恰是这种“和稀泥”式的行政干预,让事情偏离了正常轨道。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在公益性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援助的环保诉讼中,此类情况并不少见。
采访中,喀喇沁旗的一些基层干部对果农坚持告状的做法感到无奈。他们认为,无论在赔偿还是补偿方面,地方政府始终“偏向”于涉案果农,力争引导他们摆脱官司困扰,让生活回到正轨。然而从实际效果看,百姓们似乎并不“领情”。
相关材料显示,由于社会组织力量薄弱、诉讼成本高昂,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举步维艰。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统计,环境纠纷进入司法程序的不足1%,绝大多数都是通过行政部门处理。环境纠纷量持续增多和环境公益诉讼量很少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
“环保类案件胜诉率并不高,而政府的行政干预让此类案件的诉讼难上加难。”刘湘说,他接触的许多环保诉讼案件中,始终难以摆脱行政干预的影子,官司拖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屡见不鲜。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王灿发等专家表示,有的环保纠纷官司一打就是十几年,污染企业都没了,有的原告也去世了,可是官司还在打。在旷日持久的“拖”和“磨”之中,不少群众被迫放弃诉讼,部分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处罚。
"拖’和‘磨’的做法往往导致两败俱伤的结局。”刘湘认为,在环保案件中,一切应以法律为准绳,政府只有停止行政干预,法律部门从速办理,不违规、不护短,此类诉讼才会回到健康轨道上来。
有法律界及环保人士认为,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环保执法力度的加大及环保司法制度的日益完善,一些“隐性”和“潜伏”的环保案件将陆续涌进司法领域,采取司法手段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也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常规模式。法院在治理污染、维护群众环境权益上也将发挥着更为明显的作用。
业内人士表示,政府应尊重群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对于涉及环保纠纷的相关鉴定,政府部门不能“有利于企业”或“有利于舆论”就进行公开,反之则隐瞒或干预鉴定结果,更不能做“烂尾”鉴定。政府及法律部门在处理环保纠纷、案件时,必须遵循公平正义原则。